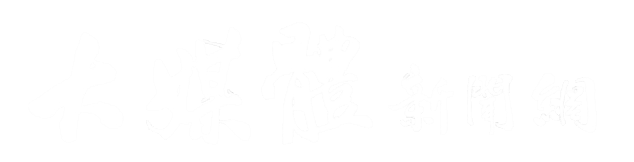【特約撰述/郎亞玲】
許多超過三、五十年的經典電影,拜近年數位修復之賜,讓年輕的影迷族群可以一睹風采,讓中老年人士,則能溫習回味。一直被視為經典中的經典的《禁忌的遊戲》(Jeux interdits1952)又譯作《無情戰火有情天》、《偷十字架的小孩》,是歷來影史討論到反戰必然會點到的經典,乃出自法國導演雷尼克萊曼(Rene Clement1913-1996)所執導。他是法國新浪潮電影崛起前法國最知名的導演。他的名作還有《鐵路英烈傳》(1946)、《陽光普照》(1960),前者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,後者為影星亞蘭德倫(Alain Delon,1935-)成名之作,1999重拍為《天才雷普利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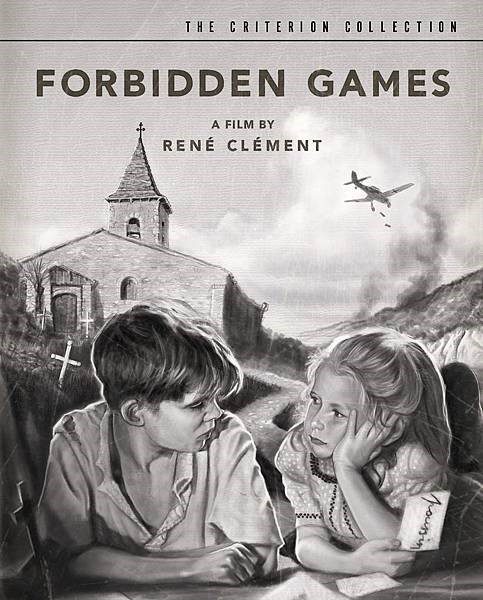
本片改編自佛蘭柯斯·波耶(Francois Boyer)的小說《禁忌的遊戲》,為黑白片,卻和整部電影的調性-講述戰爭下人們生存的困境,不謀而合。導演將文字符號化為影像符號時,運用了鏡頭的對比的手法,將「死亡」的意象層層堆疊、步步推敲,並在成人/孩童、謊言/真實、儀式/遊戲的反差,甚至仁慈/冷漠、宗教的善/戰爭的惡的對照下,產生巨大的反諷與嘲弄。本片的經典插曲「愛的羅曼史」是西班牙吉他大師拿西索.耶佩斯(Narciso Yepes)特別為本片所作,曲調反覆的撥弦聲,像來自不明遠方的戰爭與死亡的預言,與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
片子開頭就是一大批民眾逃難的畫面,父母在躲空襲中喪身,倖存的五歲女童叫波蕾,遇到了鄉下八歲男童米榭,便隨米榭回家,暫時棲身。波蕾曾目睹父母的死亡,基於對死亡的悲傷恐懼,她想給愛犬諾克舉行一個葬禮,可說是一種心理補償。米謝為討好波蕾,因她希望諾克的墳前也像人一樣插上十字架,米榭於是開始費盡心思,到處搜刮十字架。至此,電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命題:戰爭的源頭究竟來自何處?死亡的陰影又是如何造成的?答案也許不像一開始我們所認為的那麼截然二分,無論是謊言/真實;宗教的善/戰爭的惡;成人的儀式/兒童的遊戲;愛的仁慈/死亡的冷漠,二者都並非各自獨立,涇渭分明。

當波蕾的墳場日益擴大,埋葬的物種體型也越來越大,只要米榭不從,她就表現出不滿的情緒,逼得米謝全力要完成這個動物墳場!而同時米榭偷來的十字架已不再能滿足她,二人開始覬覦教堂裡的十字架時,戰爭和死亡的底牌終於昭然若揭,那就是「慾望」的驅使。即便是孩子純真的「愛」也掙脫不了「慾望」的本質,以此影射成人世界的罪行,乃是不由自主地,一步一步朝著了扭曲與墮落的方向行進。孩子的「謊言」、孩子的「偷竊」、孩子的「殘忍」,孩子看似無傷大雅的「遊戲」,其實都是拷貝自成人世界的「藍本」,二元對立的概念其實界線曖昧、相生相剋、循環反覆。善良的摧折、純真的斷裂,都只是罪惡一體的兩面而已。

《禁忌的遊戲》-遊戲即遊戲,本不該有何禁忌。正是遊戲脫離了遊戲的本質,才有「禁忌」可言。沒錯,偷靈車上的十字架是禁忌的遊戲,偷墳墓上的十字架更是禁忌的遊戲,偷教堂裡的十字架,更是甘冒大不韙,不可寬諒的禁忌遊戲。然則,比起成人世界被欲望驅使而爭名奪利,比起人們編造謊言而大動干戈,比起眾人殺人不眨眼、烽火連天,這所謂的「禁忌的遊戲」還真是小巫見大巫。代表上帝的愛,基督的救贖的十字架,對照目下充滿罪惡、欺騙、戰爭、死亡的現實的人生,但願不是劇中孩童嬉戲的玩具而已。最後,波蕾被社工人員帶走,米榭嘗試說出十字架的下落以交換波蕾留下,但徒勞無功。片尾波蕾呢喃著米榭的名字,身影消失於人群之中,令人不勝唏噓。戰火下被摧殘的靈魂,在每個時代、不同的國度,一再地被複製,被禁忌的遊戲操弄著命運。

本片得獎無數,曾獲1952年第13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、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電影。1953年奧斯卡榮譽獎(頒發予首次在美國發行的最佳外語電影)。1954年: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最佳電影。
(本文作者郎亞玲,頑石劇團藝術總監與編導,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,逢甲大學、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