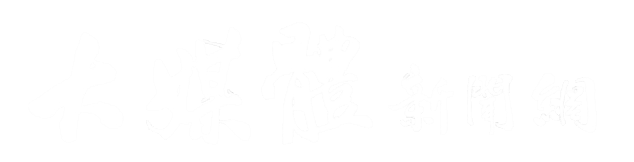【特約撰述 / 王暉之】
好畫有兩種,第一種初看時並不驚奇,圖像傳統,筆墨內斂,可越琢磨越覺出韻味,方知那老練筆墨能蘊含無盡的生命況味;第二種造形奇倔、色彩鮮爽、生氣活脫,第一眼就使人驚艷,又因其不失底蘊,驚嘆過後仍留有絲絲餘韻。我見過這兩種好畫,出自同一畫家之手,他是當代廈門水墨畫家許文厚先生。然而令人感傷的是,認識他的時候便已註定無緣再見。

許文厚先生1944年生,2009年因病逝世,終年65歲。他過去任教於福州大學工藝美術學院,也是中國美術協會會員。他是廈門市應邀到國外參展、訪問、交流次數最多的畫家,足跡遍及美、日、德、法、新、馬等國,豐厚的國際經驗與視野,必然使他認真思考水墨畫的創新課題。
許文厚早年的花鳥畫筆墨縱橫、雄強古樸,頗受他的老師李苦禪、朱屺瞻等近代大師的影響;其後在民間采風,以富有裝飾性與現代畫面構成的方式描繪惠安女等民俗題材;但他以古人為題材的寫意人物畫創作幾乎不曾中斷,晚年更進一步將人物造形誇張化、趣味化,創造了一系列憨趣的「唐女」形象。筆者以為,許文厚最大的成就便是寫意人物畫與變形唐女畫,在生命的最後幾年,他彷彿傾盡熱情般,創作了大量的這兩類作品,畫風成熟、畫境圓融,可謂巔峰之作。

春蠶到死絲方盡,他在最富創造力的年紀離世,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遺憾。據其學生講述,許先生個性率真樸素,能毫無保留地釋放與人交流的快樂,卻也深藏一份知音難覓的孤世情懷。由於長年為學校所羈絆,當他終於能夠退休時,便如籠鳥池魚復歸自然,激越狂喜之情溢於言表,從此得以嘯傲湖山、逍遙物外。

許文厚曾引用唐朝符載的畫論「已知遺去機巧,意冥玄化,而物在靈府,不在耳目,故得於心,應於手」,以應證創作中體驗與個性的重要。所謂「遺去機巧,意冥玄化」,即忘掉筆墨技巧,進入冥想的內在體驗;「物在靈府,不在耳目」,則是物我兩忘,不落於視覺形貌,而以自我精神去感知對象物的精神。
中國人物畫很早就確立了傳神的審美觀,如東晉顧愷之的「遷想妙得」「以形寫神」。許文厚深得傳神之妙,畫古人則古人神采如在眼前。屈原、李白、懷素、八大山人,究竟五官身形如何不重要,重要的是表現他們或吟嘯或揮毫、或悲世或曠達的精神風貌,這是情感與精神的共鳴。

從寫意人物畫的發展脈絡來看,五代至南宋可謂高峰,且普遍受到禪宗或道家思想的啟發。如石恪〈二祖調心圖〉、晁補之〈老子騎牛圖〉,筆墨簡潔、濃淡相參而逸氣橫生;至梁楷〈潑墨仙人圖〉,筆法更加簡率,墨氣淋漓而人物神氣完足。許文厚的寫意人物畫,直承五代兩宋的筆墨風格,而在墨色渲染層次、畫面布局張力上更進一步。小處用筆,寫人物神情;大處落墨,造氤氳之境。墨韻淌滉,人物超逸,禪意空靈,正是畫家心中之境。

而頭大身小、造形拙趣、神態憨喜的唐女形象,襯以茜紅、鵝黃、粉青的鮮美色澤,鋪陳於視覺錯綜、遠近不分明的扁平空間,則是許文厚往當代視覺邁進的一次繪畫變革,也隱約看出從明朝變形主義畫家陳洪綬得到的啟發,只是比陳洪綬更簡率、更自由。唐女們嬌眼半閉、雲髻高聳,或騎馬或提燈,嬉笑遊樂,把紅塵的繁華眷戀都形諸紙上。
值得注意的是,畫家捨棄了堅勁的線條,而以顫抖的筆觸,彷如速寫般捕捉人物輪廓,這種不經意的線條生成另類筆趣,與朱屺瞻的「落筆有時要邋遢三分,姿態轉妙」,可以相參。許文厚的女兒同時也是畫家的許曼克說:「唐女有如屈原筆下的香草美人,是父親內心深處對美善與自由的嚮往,處世內向的父親只有在作畫時才是灑脫奔放的。」

在高士身上寄託飄然世外的隱逸精神,在唐女身上留駐塵世與青春的歡樂,這兩種心情,帶著些許碰撞,卻也契合生命最真實的想望。就像我們在作品中懷想許先生的精神風貌,或許是另一種遇見吧。
(本文作者王暉之,長年從事藝文推廣,目前擔任策展人及藝評人的工作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