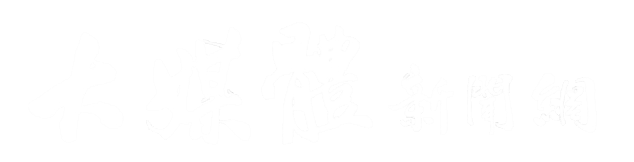【特約撰述/郎亞玲】
將這兩部片子擺在一起推薦,一方面是因為片子的時代背景都和德國納粹統治有關,同為戰時歷史記憶與國家暴力的描述。一方面則是片名的異曲同工:《波斯語課》(Persian Lessons2020) 改編自德國作家沃夫岡‧柯爾海斯所著的短篇小說《語言的發明》。而《偷畫男孩》(The German Lesson2021),改編自德國當代小說家齊格飛.藍茨(德語:Siegfried Lenz;1926-2014)同名經典小說《德語課》,本書名列世界50大小說之一,也是德國中學生的指定讀物,在德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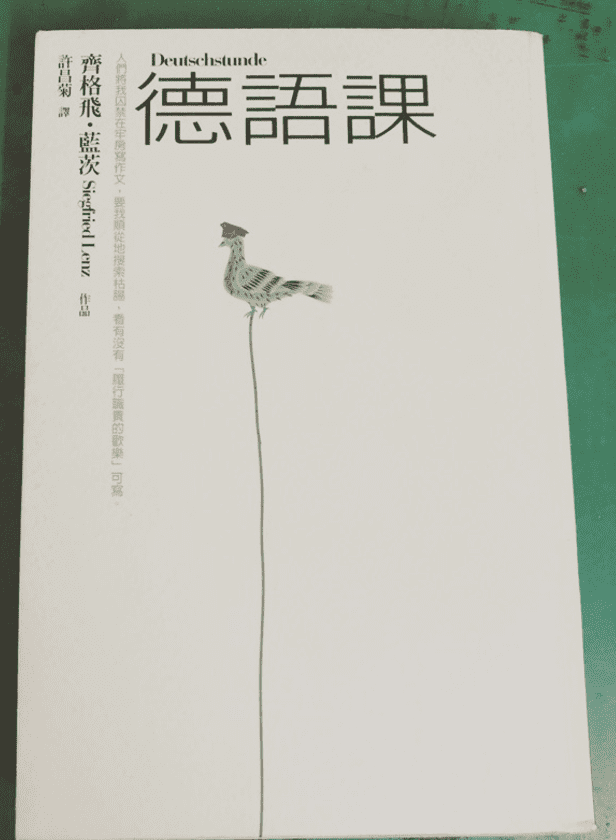
很多描述德國納粹時期統治的電影,多半描述納粹對猶太人迫害的慘無人道,或控訴人權被侵害剝奪的慘況。刻劃人性承受壓迫的堅忍和韌性之餘,也環繞在主要角色面臨各種人性的掙扎。換言之,角色與人性是核心,描述人的喜怒哀樂及生離死別,以及人面對各種嚴苛處境時所做的抉擇。由於每個情節的推進都如此扣人心弦,因此讓觀眾無時不刻感受到恐懼和死亡的壓迫。

然而,這兩部電影的主角卻似乎不是「人」,而是語言符號和視覺圖像。而這些語言圖像都被賦予巨大的生存象徵。在人命關天、命繫一線的危急存亡之秋,語言的真偽、藝術的存亡,鋪陳著生存法則,進而左右了人的命運。所以說,語言和圖像其實很政治,語言不只是語言,藝術也不只是藝術。
《波斯語課》的男主角其實是猶太人,他在臨行前不意聽見行刑主管想學波斯語,於是謊稱自己是波斯人,而逃過一劫。這個謊言幾次差點被戳破,但主角冷靜沉穩,加上人緣不錯,終究不露破綻,直到遠離集中營,觀眾不由得為他捏把冷汗。最令人動容的是他編造的語詞,全來自集中營囚犯的名字,戰後卻成為這些亡靈唯一的輓歌。

《偷畫男孩》的男主角,從兒童到青少年,親眼目睹身為納粹警察的父親,如何以執行當局「禁畫令」為由,要求兒子監督畫家埃米爾諾爾德(Emil Nolde,1867-1956 德國表現主義畫家)。然而他自己跟隨畫家學畫,更培養出收藏作品的癖好。在親情與友情逐漸高升的衝突下,壓抑與解放的多重矛盾中,男主角逐漸發展出一種扭曲的人格。一方面被父權剝奪了生活的自主性,另一方面則形成以「偷畫」為樂的情緒出口,藉以平衡身心,直至進入感化院接受管束。

也許,前面所說「這兩部電影的主角卻不是人,而是語言符號和視覺圖像。」也不盡確切,畢竟,語言符號和視覺圖像,也不過是權力遊戲的中介。冷血操作這一切的,始終是集權的體制和泯滅人性的權力中心。因此,掌握話語權的人或掌握自由創作圖像的人,在亂世,可能藉以保命,也可能惹禍上身。《波斯語課》中的男主角,以機智和創意讓語言符號不只成為保命符,更賦予了生命無價的神聖價值。《偷畫男孩》的男主角則在混亂、錯置、顛倒的政治環境下與價值觀中,始終無法讓藝術圖像成為真正的救贖與療癒。
《波斯語課》由烏克蘭裔美國導演瓦迪姆·佩爾曼執導,曾獲選為白俄羅斯代表參加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獎評選。但後因資格問題被撤銷。
《偷畫男孩》導演克里斯蒂安·施瓦科(Christian Schwochow)是當紅影集《王冠》導演。本片連獲德國奧斯卡、巴伐利亞等電影獎肯定,更跨國勇奪荷蘭海邊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。他的母親希爾德(Hilde Schwochow)擔任編劇,也是本片的推手。
(本文作者郎亞玲,頑石劇團藝術總監與編導,逢甲大學、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