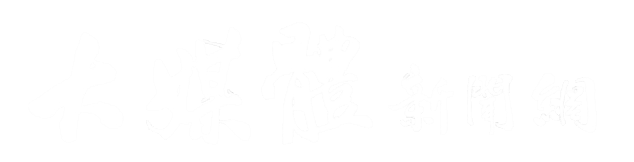【特約撰述 / 郎亞玲】
彷彿像位修行者,石德華不談作品的暢銷或得獎,十年之間,談的是生命遞嬗,自我修練的沉潛。如何層層幻化?又如何脫胎換骨?她說:三本散文集,每一本都有一個主軸貫穿。2014《約今生》談的是「由衷」,誠實面對生命、面對生死、悲傷,由衷照見。2017《火車經過星河邊》談的是「人生不空過」,相信從廢墟理站起來的人,對生命會有另一層的體悟。2020《看我,久久久久》談的是「守護」,自己積極、主動、理直氣壯地守護世間的善良。

但寫作之路從來不是她既定的人生目標,從小並沒有企圖,也沒有夢。考上中文系,老師多所肯定,自己卻是為了零用錢去投稿,並訝異於當時「皇冠雜誌社」高額的稿費。後來命運的轉折是父親生病去世,生命受苦的過程,讓她驚駭,為了排遣因疾病,因死亡帶來的悲傷、錯愕,這次她提起筆便不曾放下,也接二連三獲得了各項文學獎
總是面帶微笑她,纖手撫撥髮絲,展現無比風情,定神的雙眸,流露既溫暖又甜美的顧盼。如書中所言:「我的散文,就是我的斷代史,我沒遮掩,強也如此,弱也如此,成也如此,敗也如此,散文就是我!」又是何等堅定、自信、豪邁,這是一種「從容」。
人在紅塵中,她認為「自己」最重要,但也少不了他人的幫助,他人的成全,所以要充滿感謝。而人也是可以改變的,在《跨度》、和《左外野》二文中,她用了相當細膩的筆墨描述這種生命觀點的微妙轉折與改變。非直線/曲線、非主觀/客觀、非感性/理性,也非預設/後設的二元對立,而是曲直迴返的力道,主客之間的對調,感性理性的中和,預言和歷史的混血。像一條悠遊銀河系的雙魚座,宇宙浩瀚卻無礙璀璨,這是一種「雍容」。
在個人的價值信念上,石德華提出「信任」的重要,她認為人與人相處,簡單的善意已足,若因緣更深,則是「理解」與「信任」。至於創作的日常,則簡單而純粹,為了不致分心減損敏感度,紀律的、安靜的、甚至枯燥的生活寫真,她安之若素,這是她所謂的如佛家在紅塵中「結界」,旁人可是不得越雷池一步。她《我一個人咖啡》一文中,把這種孤絕獨立於人世,卻享受其中的氛圍,描述地令人神往。她認為生命的本質不變-荒謬、隨機、不可預設,但每個人入世的形式不同,但總有意義在過程產生,這是生命相當微妙的一部分,也道出了她人生「有容」的本質。

就她而言,而這種極其節制的生活日常,只有兩個外孫的參與,是最活潑、有趣、充滿生氣的。她說:「小孩讓我發現自己仍是個孩子,他們帶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」。她認為每個孩子身邊都需要一個「像樣的大人」,在《像樣的大人》一文中,她提到不要小看生命初起的微小而至大的影響力。她說:「現實生活中,作為阿嬤,面對孩子只想到「疼下去」。而孩子呢?看到阿嬤就飛奔過來,揹著書包,一定跌倒仆街,但抬起頭,眼睛看著你,自己站了起來,又再度飛奔過來撲向你,想想世上,還有誰會如此信賴你?」關於未來,她認為自己還在小日子裡,還是進行式,但,覺得自己不會有豐功偉業,也沒有更大的影響力。她說:「我是在世間彼此馴服的關係裡(如小王子和小狐狸),情感真誠,角色盡責的人」,對孩子、對他人,她表現出一種「涵容」的智慧,平等卻恰如其分地對應。

總是要經常回應一些喜愛寫作的朋友「如何寫作」,她說「寫作無常法」,跟個人的身世、際遇、內蘊、修養有關。換言之,寫作風格是一個人的DNA,無法仿效、學習,她舉「文者氣之所形,然文不可以學而能,氣可以養而致」(蘇轍),說明文章形式與內容都和「人」本身的氣質有關。再談到為何以「散文」為寫作重心?她提到小說寫作需要完整時空架構,更需要全心專注投入,但自己仍有生活上的許多不願割捨的事物,如讀書、演講、旅遊、陪孫子等,因此,雖然目前仍在進行「紅樓夢-新興古典小說」的寫作,但進度緩慢。即便如此,十年前丈夫去世,她在悲痛之餘,在極短時間完成十五萬字的「長生殿」改寫,曾被譽為此類作品中最上乘之作。

若以「從容」、「雍容」、「有容」、「涵容」來總結石德華的生命風采-「從容」表現在「適度」上,抽象地說是一種「速度」感,具體說是生命的「長度」,讓「存在的身體」表現出「信任」且從容不迫。「雍容」是「合度」,抽象地說是種生活「態度」,具體地說是生命的「寬度」,從「理解」的角度對待存活的生命。「有容」是「靈活度」,抽象地說是生命的不同「向度」,具體說是生命的「厚度」,以「慈悲」面對不同的存有價值。「涵容」是「恢宏大度」,抽象說是生命的「跨度」,具體說表現了生命的「高度」,以「瀟灑」的心態,珍惜當下。再度經歷丈夫病故後,石德華透過佛法,了解到「死亡是一個新的起點」,「空」不是沒有,而是「不存在」。既然不論好壞,有一天都會消失,我們能做的就是即聲即色、不沾不戀。她認為佛家的「無常」貼近了自己嚮往的「瀟灑」,也因瀟灑,讓「重情」的自己,得以有些許情感的節制。
石德華繾綣人間,在「有情」、「忘情」之間,她用華美的刻度,記下所有的凝視觀看、體貼入微與惜愛珍重。
(本文作者郎亞玲,頑石劇團藝術總監,逢甲大學、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