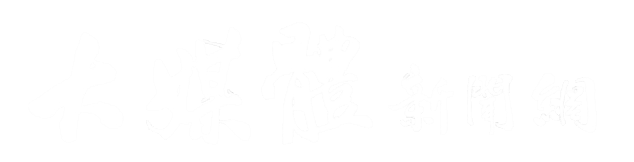【特約撰述 / 郎亞玲】
2700年前,孔子就講過「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」《論語‧子路》的話。「和」與「同」之辨,在於「自我」與「他者」之間,或是「主體」與「客體」之間,能否因自覺,而清楚地畫出一個分際與界線。擺盪在自我價值認同與群體規範利益之間,一直是人類痛苦的根源。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曾有最具代表性一句話「他人即地獄」,出自他的著名劇作《無處可逃》(Huis-clos)。意思是人若總是千方百計想要從別人的眼中尋求自我肯定,便只能從他人的凝視看見自己的存在,人生就本質而言,就不免是一場悲劇了。
這次由甫成立三年的「東海大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程」師生,推出的《寺山修司來訪/狂人教育》一劇,分別於台北牯嶺街小劇場和台中歌劇院小劇場演出。編劇與時俱進,將這位活躍於60年代,卻在當代益顯其光芒的劇場、電影、文學的前衛大師,將其成年以前的生命歷程與矛盾衝突,一併也寫入了劇本。特別是他自小「失怙」的成長經驗,對「母親」角色缺席的失落、迷惘和錯亂,成為全戲的前導與詮釋文本的線索。這段後設的編排手法,雖然對於不認識寺山修司的觀眾而言略顯晦澀,但這反而呼應了當年在小劇場運動鼓吹「觀眾參與」的他的創作觀點-讓觀眾就舞台上進行的戲劇情節動作,有更新的視角與更多層次的聯想,激發觀眾主動積極的思考,以試圖理解文本脈絡並予以再詮釋。

戲前半部描述寺山修司踏上摻雜著幻想虛擬的旅程,並與母親的各個分身互動對話,然後正式進入原作的劇本內容。原作是以「木偶劇」的形式演出,但後來多是真人以模仿偶戲肢體動作、語言,也同時和操偶人展開對話,增加全劇的「疏離效果」。劇情圍繞在一個家庭的六位性格怪異,各自有著秘密的成員,
故事線的展開源自於忽被宣告有一成員精神異常,於是成員之間相互猜忌追查真相。而觀眾就在這荒謬的情境下,和演員們一起構築出一個黑色的「童話寓言」。演員被黑衣操偶人操控,觀眾被一股無形的觀看衝動操控,其間或有理性的吉光片羽,但終究敵不過對「異己」的「霸凌」與「恐懼」,最後將最幼年的女孩送上死亡之路,成為眾人靈魂的救贖。

戲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反覆堆疊出現的「誰是神經病?」的問話,就彷彿是夢魘般的魔咒,可以說成「誰是OO?」,然後在後面任意填上自己想說的語詞;如「誰是壞人?」、「誰是小偷?」、「誰是叛徒?」………。「恐懼」並非無端而生,恐懼來自對「異己」的恐懼,人因恐懼「失控」於是濫用「權力」製造出更多的「操控」,進而令社會失控、失序,令人失德失格。毀滅異己的結果,也等同毀滅了自己與自由的可能。

「神經病」也好,「瘋癲」也好,就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傅柯而言,「瘋癲」無法定義,因為在文明發展過程中,它不斷變化,是社會權力對個體日趨嚴格的操控和管束,而強行畫出與「正常」的界限。在福柯看來,瘋癲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另類表達。羅蘭·巴特針對傅柯的巨作《古典時代的瘋癲史》說道:「歷史需要重新揭示,瘋癲不是一種疾病,而是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感。福柯從未把瘋癲當作一種現實的功能。在他看來,它純粹是理性與非理性、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應」。

這齣劇的演出因正值疫情而有所延宕,但整體製作在蔡奇璋主任與導演黎煥雄導演的指導下,突破萬難而有令人十分驚豔的成果。無論是演員如玩偶般僵硬誇張之「異化」表情與肢體、絢麗浮誇的服裝樣式與髮粧,都盡可能呈現寺山修司式的炫目視覺元素。道具、舞台的靈活多變化地運用,使舞台空間更加擴散延伸。而現場帶有即興式的伴奏與演唱,也增加了整齣戲節奏的流暢性。導演是八零年代台灣小劇場運動的健將,和寺山修司一樣具有詩人背景,這齣劇,讓人嗅出向寺山修司「致敬」的味道,紮實且餘韻無窮。「這是送給年輕人的一個「黑色童話」-青春,是殘酷的」導演說「但要做自己!」

(本文作者郎亞玲,頑石劇團藝術總監,逢甲大學、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