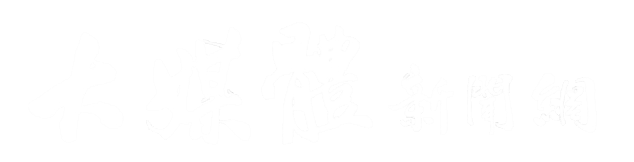【特約撰述/郎亞玲】
韓籍大導李滄東(1954-)的電影,細膩婉轉,一看再看,依然耐人尋味。這兩部電影的共同特色,即是片名都具有相當的「隱喻性」。《生命之詩》(2011)的「詩」,透過了一個垂暮之年的單身女性,所寄託的生活熱情和生命意義,然而,俗見所說的詩的美好遐想,透過故事的鋪陳,卻隱身著出乎意料的醜陋罪惡,那就是女主角一手撫養到15歲的外孫,竟是一個強暴女同學的惡性重大的青少年。

故事線一邊娓娓道來到來一位生活拮据的婦人,自食其力,雖靠照護老殘維生,卻總是用心穿戴,顯現她自律自愛的人生態度。當她踏入文化中心報名寫詩班時,我們不覺感受到在沙漠中開出的花朵,多麼令人鼓舞感動,無論她寫不寫得出詩,那份對詩的嚮往也令人動容。她以美麗自持、心中有愛,另一邊黑暗風暴卻悄悄襲來,鋪天蓋地的罪惡感從此日夜糾纏,生活頓時如烏雲罩頂。鉅額的賠償費讓她不得不向照護的病人勒索,更是讓她內心倍受煎熬。
不似多數韓片喜以誇張激情的演技和跌宕起伏的情節取勝,導演平鋪直敘,以客觀冷靜的手法呈現,女主角即便身陷「罪惡感」與「愧疚感」的漩渦,情緒仍多不外顯。「詩的美好」就她一步步走上人間絕境而言,並非反諷,而是導演精心設計要詮釋的人生實相:「美」無法獨立存在,獨立存在的美往往失之膚淺與表象,真實的「美」必伴隨「善」與「真」,無論是因道德感的自我譴責,或是因刻骨銘心的痛而走上絕路,女主角的死亡是一種對真理的渴望後的自覺,是一種牲祭的神聖與殉美的莊嚴,也是「詩」的極致境界。

至於《綠洲》(2002)的敘事則恰恰相反,《生命之詩》是美中不足,《綠洲》卻是醜中致美。男主角是個智能不足又行為粗俗猥瑣,見之就想退避三舍的男人。女主角則是天生的腦性麻痺患者,面容扭曲且行動不便。二人都是社會中具有身心障礙的邊緣人。表面上,他們的父兄並未遺棄他們,都提供了表面上起碼的食衣住行的照顧,但骨子裡另有文章。前者因為兄長車禍肇事,自己又無法承擔生計,於是被迫理所當然地頂替入獄。後者以身障者身分獲得國民住宅,但得以享受新居的只有哥哥一家人,自己卻被留置在老屋獨居。

「綠洲」象徵的是醜陋、扭曲、殘破的面容與身體之下,有一個正常人無法迄達的心靈沃土,因為人們的成見與歧視阻擋了洞見的能力。俗見以為身體的殘障亦即心靈的殘障,殊不知如此的誤解也正襯托出所謂「正常」的表象之下,其實是更醜陋、殘缺的一顆心。我們無法想像殘疾人士也擁有情慾,更不敢相信他們有能力愛人,我們總覺得他們「好好待著」就好,不要害自己和家人惹麻煩就好。我們不知不覺剝奪了他們生活的自由與生命的自主性,更將之禁足、去性,假各種「暴力」的手段,以令他們符合自身的利益。
戲中的高潮是殘疾的男女主角真的談戀愛了,他們只是做任何戀愛中年輕男女做的事,外出、逛街、用餐、做愛…,但卻引起軒然大波。諷刺的是原本對他們不屑一顧的家人們,卻突然冒出來以「照顧者」自居,阻擋他們的愛情。但對兩個生命同時尋覓到愛情「綠洲」的人而言,再多的阻擾也只是狗吠火車而已。
這兩部電影都充滿了人道關懷,但《綠洲》曾獲59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與最佳新人獎。《生命之詩》則勇奪63屆坎城影展最佳劇本,與亞州電影獎最佳導演。兩片相較,後者又比前者更不慍不火,含蓄不露,這是導演火候俱足時臻於化境的表現。二者都是導演要詮釋的一種,隱藏在醜陋、扭曲、抑鬱、卑微、殘缺….下的美,亦即醜惡背後的最真實的一種美。然而要遇見這樣的美,不能靠人為,也無法矯飾,只能靠直覺的良善與天啟的良能。

在《生命之詩》裡,女主角最後透過「詩」獲得救贖,但在此之前,她只能踽踽獨行、旁敲側擊,直至她歷經世事滄桑,穿越並承擔他人的罪惡,終能寫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生命樂章。《綠洲》中的男主角在獲得真愛之前,也只能一再承受不該加諸其身的責罰與凌辱,直到他坦然付出真愛,也獲得回饋與共鳴。
美麗就住在醜惡的隔壁,良善卻不識得邪惡的面目。愛,有時注定要被命運捉弄、主宰,有時又被權勢扭曲、踐踏。最後,《生命之詩》的女主角用「死亡」成全了「命運」之「詩」,是悲劇。《綠洲》的男主角用「命運」成全了「愛情」的「綠洲」,是喜劇。無論是悲劇或喜劇,無善不惡,無惡不善,人生的悲喜,就隱藏在肉眼看不見的縫隙裡,值得品味,我想這是李滄東想說的。
(本文作者郎亞玲,頑石劇團藝術總監與編導,逢甲大學、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)